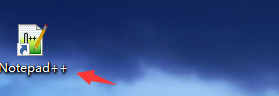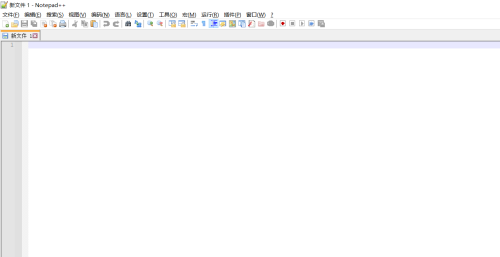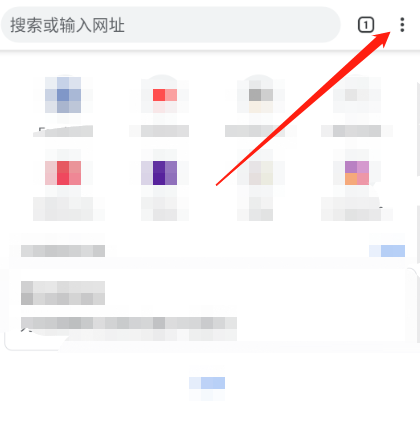太行风|擂响时代的鼓声——我所知道的抗战诗人田间
2023-05-05 07:48:32来源:燕赵都市报纵览新闻
擂响时代的鼓声
 【资料图】
【资料图】
——我所知道的抗战诗人田间
我到河北省文联工作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那时候省文联有一批大师级的作家和诗人,从那时起,我就在编辑、写作上跟他们有了交往。很多年过去了,当我再想起他们的时候,突然发现我现在的性格和生活姿态都有他们的影子。那一代人,在我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说起那时的省文联,首先会想到田间先生。以田间作品为代表的抗战诗歌,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在我的眼里他是诗人,也是英雄,虽然个子矮小,但在我心中形象高大。
田间。 作者供图
一
田间是一位大师级的文学前辈,但在我的印象中,他也是一位老人,是一位有个性、让人尊重的长者,他是我见到的能称得上“大师”的作家中最具诗人品质和性格的老人。
诗人田间在大家熟悉的名篇《假使我们不去打仗》中写道:“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这首诗激发了当时中国人内在的精神力量,它的热度一直持续至今。我查过资料,1935年至2006年之间,田间出版了60多部著作,这个数量是惊人的。
田间是一位大师级的文学前辈,但在我的印象中,他也是一位老人,是一位有个性、让人尊重的长者,他是我见到的能称得上“大师”的作家中最具诗人品质和性格的老人。我调到河北省文联时刚20岁出头,和田间是邻居(他家在北京,所以在石家庄也是“单身”)。当时他住在石家庄北马路19号河北省文联(那时叫“河北省文艺组”)一间15平方米的平房里,那里是办公室兼宿舍。他对诗歌的激情、他的执着、他的敏锐、他的创造力,一直到晚年都没有减退。那几年,他几乎隔不了多长时间就出一部诗集,诗集出版后,他裁一些白纸条,用毛笔小楷在上面题上字,署上名字,用糨糊粘贴在书的扉页上送给同事和诗人们,当时我为他贴过不少这样的纸条。
在我的记忆中,鲜有什么世俗、芜杂的事情能够干扰田间的创作。他的生活很有规律,很少有什么社交活动,生活简单到让人难以置信:每天早晨到单位食堂买一小铝锅粥,早晨喝一半,留到晚上再把另一半热一热,买一个食堂的馒头和一小碟咸菜丝,就算是一顿饭了。中午饭也是,食堂有什么他就吃点什么。除了参加会议,我甚至不记得他和别人到饭店里吃过一次饭。后来我做了几十年的刊物编辑和主编,也从没有让作者请我吃过饭,原因在于我从内心依然遵循着田间先生这一代人带给我的理念,少些芜杂,少些世俗,专注编辑和写作。
有人曾问我:“在写诗上,谁对你的影响最大?”我回答,首先就是田间,不只是在艺术追求上,更是在做人上。田间身上有一种独有的诗人气质,刚毅内敛,特立独行。1982年1月,田间曾经说过:“近得一封来信,是在上海共同战斗的诗友写的,他的远方来信鼓励我说‘在你的诗里,没有白发’。”我觉得这句话是对田间先生晚年创作状态的真实写照。虽然他曾担任河北省文联主席、原《河北文艺》杂志主编,但他不善于处理琐细的事务,经常听到和他年龄相近的同事在会上与他争吵。我唯一一次见到他在这方面表示苦恼,是有一天吃过晚饭,我们两个在小院里散步,我问他下午是不是又开会了,他茫然而天真地问我:“小李(我的原名叫李立丛),他们怎么总是和我吵?”对于田间的性格,他的夫人葛文这样评价:“他是一个不善言谈的人,说话吐字难成句,半句没说完,就只剩下‘哈哈’代之了,可谈起诗来,却能紧紧抓住你。”“他那全神贯注于诗业的痴态,难为一般人所理解,我终于理解了他,谅解了他痴呆中的笨拙,笨拙得那么情真。”对于俗常的事情,诸如人际关系之类,田间先生处理起来很不顺畅,很书生气,在我的记忆里,每天他基本上就是在自己的屋子里读书、写诗、写字。有一次跟书法家旭宇在电话中聊天,他谈到了一段旧事:20世纪70年代随田间到保定出差,当时的保定地委主要领导来看望田间,送走客人后田间一脸茫然地问:“刚才来的这个人是谁?”他是非常真实的一个人,充满着文人气、超然气、诗人气。
上世纪80年代田间(左)与夫人葛文(右)在北京后海家中。 作者供图
二
田间以其个人的影响力和艺术魅力把河北诗歌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田间在生活中有一些别人不理解的习惯,比如,他每天喝的茶叶要留下,第二天早晨在炉子上煮一煮,然后把剩茶叶吃掉。有一次我熬了一小锅玉米面粥,给田间先生喝了一碗,他说好喝,一定要我去给他买玉米面,他自己熬粥。第二天早晨我还没起床,他就在门外喊:“小李,快起来。”我赶紧穿衣服跑到他的房间里,原来他把满满的一大碗玉米面一下子倒进了煮开的沸水里,怎么也搅不开了。后来我问他:“您原来在晋察冀边区就没有看到过老乡们怎么熬粥?”田间木然地摇了摇头。我的启蒙老师、时任《河北文艺》诗歌组组长王洪涛也对我讲过与田间交往的一些旧事,他说:“田间人真是太好了,就是不明白那些俗气的人情世故。”
田间回北京或者去外地时,总是把他房间的钥匙留给我,替他接收报刊、信函,替他打扫卫生。而且外出时他爱给我留一些用毛笔小楷书写的便条,我记得有,“小李,窗台上的饼干快要坏了,你把它吃掉。”“刊物不要少了,放好。”“小李,去给我买一个能腌100个鸡蛋的小缸,买100个鸡蛋腌上。”由于我母亲来看我时,带来了一些咸鸡蛋,我送给了田间先生几个,他吃了之后连连说“好吃”。我和妻子就到土产商店买了一个小缸,并且按照我母亲教给的方法,把浓盐水揉进胶泥,再把胶泥裹在鸡蛋外面,给他腌了一缸鸡蛋。有一次作家铁凝对我说:“郁葱,那些小条你可该留着,都是文物。”我听了以后心痛不已,后悔当时就没有把它们保存下来。诸如此类的关于田间先生的故事有很多,有的是真实的,有的是演绎的,无论是真是假,都说明了田间独特的性格。那位老人,真是单纯、真挚而善良。
1958年以后,田间从北京调到河北工作,我现在想,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或许是由于他对晋察冀边区的感情。除了曾长期在晋察冀边区工作之外,1948年冬天,田间还曾经担任张家口市委宣传部部长,1949年,他兼任察哈尔省文联主任。1973年春夏之交,应作家、编辑家康迈千等所邀,孙犁到石家庄小住,看望他的老战友田间等人,住在了北马路19号作家李满天的家中。北马路19号是一个文化大院,河北省文艺组、原《河北文艺》编辑部、河北省出版局等单位都在这个大院中,李满天的家就在河北省文艺组五排小平房的最后一排。那几天,几位作家一直陪着孙犁,白天走访,晚上聊天。当时田间担任河北省文艺组的主要负责人,工作繁忙,但他还是抽出了一个星期天和康迈千、李满天、张庆田一起陪孙犁游览了正定古城。
1958年5月14日,刚刚担任河北省文联主席、原《蜜蜂》文学月刊主编的田间在怀来县花园乡南水泉村主持召开了诗歌创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除了河北省20余位重点诗歌作者之外,还邀请了国内著名诗人徐迟、邹荻帆等人到会,田间以《谈诗风》为题做了发言,提出了“开一代新诗风”的口号,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河北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诗会”。《蜜蜂》文学月刊在当年的7月号推出了“诗歌专号”,那一期的专号从内容到装帧都很经典,至今我还记忆深刻。田间以其个人的影响力和艺术魅力把河北诗歌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南水泉村的诗会之后,与会诗人韩放、叶蓬、韦野等以及当时的青年诗人何理、刘章、浪波、王洪涛、申身等迅速成熟,在《诗刊》和其他刊物发表了自己的代表作。田间在艺术上非常包容,鼓励用多样化的创作形式进行诗歌写作,比如上面提到的几位诗人,他们的生活经历、写作风格都有差异,但是田间对他们的写作投入了同样的热情,倾注了同样多的心血。葛文回忆说:“1963年,战士王石祥(河北邢台籍诗人)把他的诗稿拿给田间看,田间兴奋地称诗人的情绪是诗的情绪,是诗歌的情绪。1978年,田间带病多次给在邯郸工厂的孙桂贞(伊蕾)写信,谈诗之源、诗之本,原信均用毛笔小楷书写。”诗人浪波曾经对我说:“田间对河北诗人的托举和精神涵盖力是巨大的,对河北诗歌的影响是巨大的。”
田间平日里话不多,每天都写诗到很晚,有时他半夜叫我:“小李,来看看我的诗。”他在写作诗集《清明》的时候,经常熬到凌晨三四点钟,我那时候也爱熬夜,河北省文联小院里一老一少,窗口的灯光总是亮着。一天晚上,我向他请教抗战时期在延安兴起的群众性诗歌运动——街头诗运动,老人的话突然多了起来,他说自己的诗歌“最有价值的就是那个时期的,那时候把自己写的诗篇写在墙壁上,写在岩石和大树上,鼓舞军队和人民的斗志”。那些作品很多成为抗战文学的经典,看得出来他对那种生活状态依旧充满着向往。我问他,闻一多先生是怎么称他为“擂鼓诗人”的?田间用浓重的安徽无为口音说:“一声声的鼓点,不只鼓的声律,还有鼓的情绪。”后来我查了资料,一字不差。实际上,我们现在谈抗战文学,有一个现象或者说现实被忽略了:真正写作于当时、直接作用于那场战争、后来成为经典的文学作品,在冀中这一带,田间等诗人创作的诗歌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三
至今,想起田间先生的时候我就觉得,一个诗人,当有一天终要离去的时候,仅仅有两点能够留下,也仅仅这两点有意义,那就是人的品格和文字,还有一个人厚重的、永恒的背影。
那时我写了诗,当然要向田间请教,隔代人的交往,很自然,很自如。田间先生让我记忆深刻的一件事是:我和他做了几年邻居,经常请他看我当时写的诗,认为还可以的,他就把那一页折一下说:“去交给洪涛吧。”不满意的,他就直接说:“这些不行。”从来没有听他说过那些诗为什么“行”,为什么“不行”,他也没有对我讲过应该怎样写诗、不应该怎样写诗,这对我后来的影响极大,使我悟出了四个字:诗不可说。我总想,也许田间先生想告诉我,诗可“悟”而不可“教”;也许田间先生想告诉我,诗可“异”而不可“同”。他对我说过许多话,唯独很少对我说最应该说的诗歌。前面说过,田间对世俗的事情知之甚少,也不大顾及那些你来我往的俗事,外人看他生活中似乎有些木讷,但是只要进入到诗歌里,他思维的跳跃、语言独特的魅力一下子就都迸发出来,那时就显现了他过人的智慧。我曾经对一位诗友说过:与大师交往,感觉不一样,他们身上那种超出常人的状态,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我的性情和诗情,我好像也从他的身上获得了某种才情。
老人也有忧虑的时候,这让我想起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歌德”与“缺德”》事件。文章《“歌德”与“缺德”》发表在1979年第6期的《河北文艺》上,被称为“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大潮中的一股逆流”,受到了媒体和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批评。作为河北省文联主席的田间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有时候看他有些焦虑,但更多的时候他很坦然、很淡定。葛文在回忆这一段历史的时候说:“田间以一颗赤子之心,承担了作为省文联负责人应负的责任,从不辩解,任劳任怨,一如既往,探寻希望之岸。”《“歌德”与“缺德”》的作者李剑以及河北省文联的领导被中央领导请到了钓鱼台座谈,坦诚、宽容、开诚布公地讨论各自的观点,使得文艺界的思想解放大大地向前推动了一步。当时田间本来压力很大,但从北京回来后一改愁容,神情舒朗,这对于一向不苟言笑的他来说是很难见到的。看得出来,他的内心已经释然了。当时担任《河北文艺》副主编的肖杰也在1979年8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歌德”与“缺德”》文章一事思路应该是着重讨论问题,不应相互扣帽子。
他们那一代人的坚韧、真诚和善良是天生的。2015年春节前夕,我专程到北京后海看望作家葛文,快到北京的时候临近中午,我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我一会儿就到,没想到路上堵车,一直到将近下午一时才赶到后海北沿田间先生的家门口,远远就看见葛老在胡同口站着,见到我后,她说:“放下电话我就出来等,等着你来。”当时我眼泪就掉下来了,老人那年94岁了,天那么冷,竟然为了等我在胡同口站了将近一个小时。回石家庄的路上我一直懊悔,责怪自己为什么要提前给老人打那个电话。在老人的家中,她一直拉着我的手,说起了田间和河北省文联、河北省作协的一些往事,说起了她在意的事她惦记的事,有的让我感慨,有的让我惭愧和动情,一直到葛文去世之前,我都与她以及田间先生的女儿田春生保持着经常的联系。
最近翻看旧笔记本,里面记载着一段往事: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晚上,田间先生罕见地与我聊起诗歌,先生拿出一个16开本的油印册子说:“你拿去看看,看看我过去的东西。”回到宿舍,我打开那本册子,上面有先生发表在1942年2月4日《晋察冀日报》上的文章《文学上的一次战斗》,我把其中的一些话抄在了笔记本上,其中写道,“作家要用自己的血来写作,对生活有热情有爱,对战斗有热情有爱,作品中才可能也表现出这种热情来。”那段话很长,我在笔记本上抄了几页,之所以引用其中的一节,是由于我觉得很惭愧,抄下这段话之后,我并没有认真再读,其中关于如何写诗,写什么样的诗,田间先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如果年轻的时候能认真领悟他的论述,在写作上或许比现在要更长进一些。
至今,想起田间先生的时候我就觉得,一个诗人,当有一天终要离去的时候,仅仅有两点能够留下,也仅仅这两点有意义,那就是人的品格和文字,还有一个人厚重的、永恒的背影。(郁葱)
关键词: